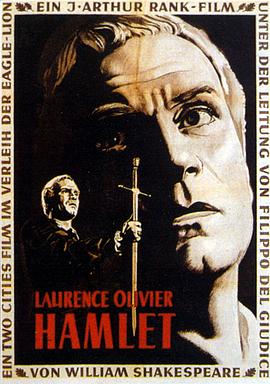一个笼子在找一只鸟(二)
——读卡夫卡手记之三十七
文 | 梁长峨
一
“一个笼子在找一只鸟”,是卡夫卡在他的箴言录中写下的文字。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卡夫卡说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所指的是什么?
这句话是暗喻。根据此暗喻,和卡夫卡一生作为及某些言语,我们不妨作个推想。
这个“笼子”是文学创作,而这只“鸟”就是卡夫卡。卡夫卡为什么会像需要一个温暖安全的家一样,需要文学创作这个笼子,而且心甘情愿地飞入这个笼子,并以“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终生囚禁在这个笼子里,为笼子而献身呢?
二
读卡夫卡,总觉得青春年少的他,精神苦闷,心里冰冷,异常孤独,一颗骚动的心和一双走投无路的目光在找寻。他说自己“遍体鳞伤,百般痛苦”,内心世界是一片“冰封的大海”“寒意整天追逐着我”。
一个年轻轻的孩子,血液本该在皮下滚滚涌流,不停向外喷发热浪,时时显现蓬勃的气象,为什么却会感到苦闷、孤独、浑身充满寒意呢?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的混乱、文明的倒退、人性的凶恶、政府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不能不让年轻的至真至诚至纯的卡夫卡睁大惊恐的眼睛,感到浑身浸透了彻骨的寒意。卡夫卡那双明察秋毫、锐如利剑的眼睛,比一般同时代人更深地看透了当时社会的丑恶本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心里形成一个“冰封的大海”。
三
怎样才能击破心中的冰海,如何消弭彻骨的寒意?他找遍世界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寻寻觅觅,最后不幸王国的王子走入文学境域。他双眼充满了喜悦,发现文学的境域霞光灿烂、生机勃勃。从此认定,文学创作才是他唯一的避难所,在这里才能找到适合戴在他头上的王冠。
自从他认定写作是自己的宿命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头。他给好友马克斯写信掏心说:“不写作我的生命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而告终……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美妙报偿……作家的生存是依赖于写字台的,只要他不想摆脱疯狂,他就绝不能离开写字台……对写作的渴望无论在哪里都大大重于其他……”
他给女友说:“我感觉到,倘若我不写作,我就会被一只坚定的手推出生活之外……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地狱,我是通过写作。所以在不得已时,亦只能通过写作,而不是通过安静和睡眠以求留在人间。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赢得写作,不如说是通过写作获得安宁。”
读这些文字,我们似乎听到卡夫卡血液里汹涌着写作的涛声,一阵阵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在他的心海翻腾。他的骨髓已经铸就终生写作、什么都不能摧毁的意志。对他来说,不写作就等于疯狂向他挑战,他写作,他存在,不写作,无异于死亡。在他眼里这个世界魔鬼成群,他不愿与这个肮脏的世界为伍,他只有写作这一条路,于是他要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鲁滨逊插在海岛制高点上的旗帜”。
四
文学创作与办公室工作有巨大的反差,相互排斥,势如冰火。写作需要静心专一,它的重心在深处,而办公室工作则浮于生活的表面,团团转悠,相互牵扯,机械重复。这样,身兼两职的他必定陷入不可调和的巨大的矛盾之中。
卡夫卡在日记中万分痛苦地写道:“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我成了一家社会保险公司的职员。现在这两种职业绝不能互相忍让,绝不会产生一种共享的幸福。一个中的最小的幸福也会成为另一个中的莫大的不幸……每件公文我都尽快处理,尽快往下传。然而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了结。我在思想上继续跟着公文,从一个处到另一个处,从一张办公桌到另一张办公桌,沿着一条手的链条,直至收件人。我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冲破我办公室的四堵白墙。然而我的视野不是更宽广,反而更缩小了。我也跟着缩小。”他常露出苦笑:“我是一块破烂,甚至连破烂都不是。我不是滚到轮下,而是滚到一只小小的齿轮下……”
没有感同身受到切肤之痛,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卡夫卡就是一个黏黏糊糊的职员蜂房里的蜂,天天自己编造、接受、传递、解释、处理文件,沿着办公室的链条不停地飞来飞去。有时为了一件讨厌的公文,他不得不从自己的“躯体”上割下一块肉来。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呀!在写十行要受十次惊的办公室里,文学创作,免谈。一个朋友去看望他,卡夫卡隔着公文堆示意说:“我从我的纸牢里向您致意。”这个幽默含着多少苦汁啊!
人们无需用特别锐利的目光,就能看到,公务员生活对卡夫卡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他常常脸色灰黄,弯着腰,缩着身,坐在光洁的大办公桌后面,公文之林把他全部掩埋了。
五
“我的职业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唯一的要求和唯一的职业,即文学是相抵触的。由于我除了文字别无所求,别无所能,也别无所愿,所以我的职位永远不能把我抢夺过去,不过也许它能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
为了不被毁了,他坚持夜里写作。他每年至少若干个月下午下班回来,吃完饭,躺下,睡到七点至八点,散一小时步,然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一点或二点。他只知道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外边什么事都不问,且特别怕人干扰。他还常常因激情过于澎湃,陷于其中不可自拔,通宵达旦地写呢!
著名小说《判决》,就是他一个整夜一气呵成的。他说从晚上十点写到凌晨六点,他一直坐着写,脚都发僵了,几乎不能从写字台底下抽出来。当故事在他面前展开着,当他的思想感情之舟在一片汪洋上前进着的时候,他感到极度的紧张和欢乐。一切居然都可以表达,连最陌生的构想都有一片大火等候着,等候着它们在火中消逝和再生。不知不觉,窗前的天色变蓝了,一辆车子驶过,噢呀,天亮了。这时,他正写下最后一个句子。放下笔时,他感到心脏隐隐作痛。然而,他同时也感到思想感情倾泄后的无比快乐。
六
对一般人来说,生病了,要好好休养生息。而卡夫卡呢,生病了,不能上班,没公文写作和处理,没有杂事琐事干扰,是集中精神写作的好时机。一次他生了一场重病,写信给朋友说:“已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没写了。我的处境是:上帝不愿让我写,然而我偏要写,我必须写。这是永恒的拉锯,而最终上帝毕竟更强大,这里边的不幸之多超出你的想象。”
卡夫卡生来体质就弱不禁风,经常生病,后来又得了终生无法治愈的喉结核和肺病。面对疾病,他还坚持写作。他说:“宁可粉身碎骨一千次,也强于将它留在或埋葬在我心中。我就是为这个生存在世上的,我对此完全明白。”
疾病之于卡夫卡,就如永远摆脱不掉的魔鬼,缠得他不得安生。他需要经常进疗养院。然而,在这里他还是不忘写作。疗养院照明条件不好,即使写封信也使他眼睛发花。可他内心感觉到写作冲动时,这些障碍自然就不存在了。有一次,他灵感来了,他不拘礼节,吃完饭马上起身离开,像一个奇特的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径直上楼梯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椅子放在桌子上,借着装在屋顶上的昏暗的电灯泡光线写作。
他这样做,是进一步加剧生命自焚呀!
七
生而为人,情爱呀,世故呀等等,这些都是免不了的。尽管这一切都系高耗能的规定程序,但有些人却乐此不倦,不惜代价,玩得特别溜乎。这对卡夫卡而言,因写作而致全面萎缩,近乎痴呆。
1912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我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卡夫卡为了写作而在拒绝正常人生活、拒绝世俗的路上,绝对不可能回头了。
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记中进一步强调:“从文学方面看,我的命运非常简单。描写我梦一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使其他一切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没有别的任何事情能使我满足。”这时,卡夫卡正同菲莉斯处在热恋中。这则日记已经注定他同菲莉斯的爱情悲剧。
同年11月1日,他直接在给菲莉斯的信中说:“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我便等于是瘫在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这对热恋中的菲莉斯意味着什么?这对他们之间的恋爱结局意味着什么?
他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为写作设置的,如果它发生变化,也是为了尽可能更适合写作而已。他给自己开列了一份清单,列出他为写作牺牲了什么,和为写作的缘故他被剥夺了什么。也就是说,为写作所遭受的损失才是他可以忍受的,除此他都不能忍受。
八
卡夫卡太热爱太留恋太需要写作这个笼子了。一切都可以没有,唯独写作这个笼子不可以没有;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写作这个笼子不可以抛弃。写作这个笼子是他的天堂,他在这里寄托了一切,幸福、甜蜜、自由和快乐。笼子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都让他感到枯燥、无聊、庸俗和乏味。拒绝了一切世俗的东西之后,卡夫卡向更深的孤独中走去。
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这同人际关系没有直接相干,我只能以这种自成一体的、内在的关联和严格的方式来写作,并因此也只能这样生活。”
到最后,他竟然想象出这样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他带着纸、笔和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中最里面的一间,饭由人送来,放在离他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他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他唯一的散步。然后他又回到他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
这是怎样的痴迷、疯狂和孤绝啊!
九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几个月前读到的一篇短文,文中说:“任何事好玩则已,野心到什么家,那真叫一个断气。比如说作家,世故地说,我不主张那种惊天泣鬼的自焚式写作。生而为人,安然自在就好,哪有那么多英雄气短。所幸父母给了你生命,又恰好给了点所谓的禀赋,慢慢细水长流地用,就可以了。”
这自然是一种活法,是物质富裕后开始享受人生的一部分人认可的活法,是不愁吃、不愁喝,心里淡泊的一些人追求的活法,无可厚非。但是假如这个人身后有一只张着血盆大口追赶他的狼,我敢说他绝对不会还在那里说父母给的生命要“慢慢细水长流地用”,慢慢地走,千万不要跑,跑会影响心脏、影响肺、伤筋骨。他一定跑得比兔子都快,累得心脏快要炸了,肺已开始出血,他还会拼命地逃跑。
我还这样想,如果他是卡夫卡,如果他是巴尔扎克,他一定不会这样说,恐怕连想都不会这样想。创作灵感来了,汹涌澎湃,如大江决堤,势不可挡,容不得你夕月晨花,茶米初香,一点一点在那儿细细地熬。这样的时候作家就会自焚式地写作几天、几个月。有人说:“作家的每一个字都是脑浆熬出来的。”这话说得很实在,只是有点骇人、残忍。但是,所有的大作家都不怕,并乐此不疲。为了创作天才作品,他们愿一生朝思暮想,魂牵梦绕,怀疑、惆怅、纠结、难眠、激动、惊喜,钩心挠肠。所有作家临终都只有遗憾,没有后悔。这就是各人选择的笼子不一样啊!匈牙利大提琴家杜普蕾绝不会因听到同行史塔克说“像这样演奏,她肯定活不长久”,而停止演奏或改换门庭。因她就是这样笼子里的鸟。由此对比卡夫卡,岂不也是一样?不然,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各类巨人和英雄了。
作者简介
梁长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散文家》副总编、《华夏散文》副主编、曾任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出版过《今日的灵魂》《无悔岁月》《爱的心路》等随笔散文集。
 梦千寻
梦千寻